起
你是否想過一個(gè)問題,你為何是你?
我走到鏡子前,停了下來。頭發(fā)還濕漉漉的,右手手腕有些酸脹,周圍已經(jīng)沒幾個(gè)人了,零散地分布在房間各處,埋頭整理自己的東西。
我抬頭看了看墻上的鐘,一片煙霧繚繞中,指針停在了十點(diǎn)一刻。
這個(gè)時(shí)間,浴室該關(guān)門了。我伸手擦了擦鏡子上的水霧,里面映出一張蒼白的臉。老爸昨天又拿他打麻將時(shí)聽來的事情說了我一頓,真不知到底我是他兒子還是那些“別人家的小孩”是他兒子,完了還莫名其妙讓我照了半天鏡子,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!
我整理著頭發(fā),手腕上的疼愈發(fā)厲害。
我往左邊歪歪頭,鏡子里的我往右邊歪了歪頭。我仔細(xì)盯著自己瞧,鼻翼上似乎還殘留著青春痘留下的疤痕。
收拾好一切準(zhǔn)備離開,就在這個(gè)時(shí)候,我忽然發(fā)現(xiàn)什么東西不大對(duì)勁。
茶室
張是最早發(fā)現(xiàn)這問麻將室的人。麻將室背街,掛著茶樓的牌子,進(jìn)來之后繞過一條狹長(zhǎng)的走廊,就會(huì)看見一間間小屋,隔得簡(jiǎn)陋又粗糙。
奇怪的是隔音效果特別好,在里面根本聽不見其他房間的聲音。
張的丈夫是公司的中層領(lǐng)導(dǎo),大她五歲。張還是學(xué)生時(shí)就和他認(rèn)識(shí),畢業(yè)之后馬上結(jié)了婚,至今七年,正好七年之癢。張沒有工作,平時(shí)就喜歡坐在麻將室里賭點(diǎn)小錢。
丈夫經(jīng)常出差在外,就算回到家,也總是用背對(duì)著她,兩人的關(guān)系相敬如“冰”。張偶爾也會(huì)從丈夫的行李中或者衣服上嗅到不屬于自己的香水味,可他們從未想過戳破這一層玻璃紙。
“能過一天算一天唄。結(jié)婚這么久,我又生不出孩子,反正他只要定期拿錢回來,別的我也管不住他。男人嘛。”張總是一邊這樣說著一邊丟出牌來,臉上稀薄的笑容卻沒有達(dá)到眼底,反而從聲音里顯出一絲寂寞的意味。
老李抬頭瞥了她一眼,每次打牌,他總坐在張的對(duì)面,雖然只是牌友,可也勉強(qiáng)算得上熟知。這個(gè)女人三十露頭的年紀(jì),眼角爬上了些細(xì)細(xì)的紋路,卻別添了一份韻味,可以想見她年輕時(shí)的美貌。
他悄悄嘆了口氣,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家那個(gè)黃臉婆。要是那個(gè)母夜叉也能像張這樣,又賢惠又嫵媚,自己也不至于為了躲開她的大嗓門天天跑出來找樂子。今早那女人莫名其妙地發(fā)起了脾氣,如果不是他跑得快,保不準(zhǔn)又將爆發(fā)一次無意義的爭(zhēng)吵。
老李跟著丟出張牌,換了條腿蹺著,一只手探進(jìn)口袋,準(zhǔn)備摸支煙出來提提神。可指尖剛碰到煙盒,左邊就傳來一聲輕輕的,略顯做作的咳嗽。老李一頓,偷著眼角往邊上看了眼王工,又默不作聲地把手抽了出來。
王工皺著眉揉了揉鼻子,死死地盯著手里的牌。旁邊的老李很煩人,說話嗓門大,一開口整個(gè)屋子就變得跟菜市場(chǎng)一樣。而且那人還喜歡抽煙,身上總帶著嗆鼻的味道。
王工其實(shí)很不喜歡和這些人混在一起,他更希望自己能和兒子班上那些衣著光鮮的家長(zhǎng)們坐在一起,談點(diǎn)國(guó)內(nèi)國(guó)際形勢(shì),股價(jià)走向什么的。可惜兒子不爭(zhēng)氣,次次考試倒數(shù),這次好不容易走關(guān)系把他塞進(jìn)封閉管理的重點(diǎn)高中,成績(jī)還是一點(diǎn)起色也沒有。
想著想著,他偷偷看了眼身邊的袁。要是兒子和袁的女兒一樣該多好啊,王工在心里偷偷嘀咕,要是當(dāng)初生的是女兒,是不是會(huì)聽話—點(diǎn)?
“碰!”袁喜上眉梢,拎了張白板丟出來,抬起頭裝模作樣地開口,“對(duì)了,我女兒這次啊又去參加了個(gè)什么鋼琴比賽,雖然得獎(jiǎng)是好事情,但不能總把時(shí)間浪費(fèi)在這些東西上面你說是不是,以后又不當(dāng)什么音樂家。”
說著,袁稍微停頓了會(huì)兒,像是等待著什么。一桌子人保持著尷尬的沉默,直到張受不了,抬起頭接著他的話開口:“你女兒拿了幾等獎(jiǎng)?”
“一等。不過還不行啊,畢竟不是專業(yè)的,人家還有得特等獎(jiǎng)的呢——”袁迫不及待將早已準(zhǔn)備好的一肚子話傾倒出來,張皮笑肉不笑地把頭發(fā)往耳邊撩了下,側(cè)了側(cè)身子稍微躲開老李的視線,隨意附和了兩句。
袁說得更起勁了,老李盯著張的樣子,肚子里的“饞蟲”直叫喚,王工把腦袋埋得更低,狠狠地捻住手里的牌,不由自主地皺起了眉頭。如果是從前,他估計(jì)會(huì)嘟囔句:“得瑟個(gè)什么德行!”可今天他什么都沒有說。
各人手邊的茶水已經(jīng)涼了,中途那個(gè)詭異的女老板出現(xiàn)過一次,添了點(diǎn)熱水后,又悄無聲息地離開了。
桌子上的手在洗著麻將牌,屋子里響起噼里啪啦的聲音。
四張心照不宣的臉湊在一起,面對(duì)著面,就著昏黃的光線。
“你老公最近怎么樣?”袁忽然轉(zhuǎn)向張問了一句。
張頓了頓,抬起頭看著他。
異變已經(jīng)過去了三個(gè)禮拜,兩人都隱約明白了身邊到底發(fā)生了什么事情,盡管他們從未對(duì)彼此談及這一切。
留下還是離開,這是一個(gè)問題。
張
你是否想過另一個(gè)問題,你愛的究竟是那個(gè)人,還是自己的某種妄想?
那天張比以往早了半個(gè)小時(shí)來到茶室,正值下午兩點(diǎn)半。
老公打來電話,敷衍了兩句后告訴她今天不回來了。
不回她這里,就是要去別的地方。剛開始她還上門鬧過哭過吵過,到了現(xiàn)在,只剩下麻木。她說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對(duì)這個(gè)男人心存眷戀,還是僅僅因?yàn)樗屪约阂率碂o憂。
自從發(fā)現(xiàn)了這個(gè)茶室后,她開始頻繁出入這里,和不同的人坐在一張桌上玩牌,偶爾說點(diǎn)家長(zhǎng)里短,接受諸如老李這樣的人帶著欲望的打量,得到點(diǎn)可冷的安慰。
張跟老板娘打了個(gè)招呼,走進(jìn)了最里面的房間。里面沒人,她隨意走到背對(duì)門口的座位前坐下,燈光有點(diǎn)暗,她摸出手機(jī),無聊地翻看微博上的八卦。
過了會(huì)兒,門口傳來腳步聲。張微微抬起眼,老板娘提著茶壺走了進(jìn)來。那茶壺有些年頭了,黃銅外殼被摩擦得锃光瓦亮。
張稍微挪開了點(diǎn)兒,看著老板娘給她倒水。她從來沒有見過老板娘的家人,也從未見過這個(gè)女人穿別的衣服。她總是一襲拖地的長(zhǎng)裙,藍(lán)色粗布,上面繡著大朵的花,遠(yuǎn)遠(yuǎn)看上去異常鮮活。
老板娘沉默寡言,平時(shí)最多只是在給客人報(bào)賬時(shí)蹦一兩個(gè)字出來。可是今天,當(dāng)老板娘將她的茶杯傾滿,轉(zhuǎn)身準(zhǔn)備離開時(shí),忽然張的耳邊幽幽地飄過來一個(gè)問題:“你喜歡現(xiàn)在的老公嗎?”
張一愣,回過頭看著老板娘。她沒說話,也不看張,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劉海遮著眼睛,就好像剛才那個(gè)問題根本不是她問的一樣。張心里覺得有些怪,卻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,搖搖頭。
“希望他變成你想要的樣子嗎?”緊接著,老板娘又問了一句。
這次張看清楚了。那女人的嘴一張一合,動(dòng)作幅度很小,吐字卻異常清晰。
張鬼使神差般地接了一句:“要是能變當(dāng)然好了。”
“那就讓他看鏡子。”老板娘又莫名其妙地吐出一句話。
張皺了皺眉,正準(zhǔn)備問,門口傳來哈哈的笑聲:“張,今天真早啊。”
張回過頭去,老李撩開門簾走了進(jìn)來。等張跟他寒暄完,再想追問老板娘些什么時(shí),那女人已經(jīng)不知什么時(shí)候離開了。
那一整天,張都有些心不在焉,連輸幾把之后,心情更加惡劣。
她決定早點(diǎn)離開。出門跟老板娘結(jié)賬時(shí),那女人只顧著低頭找零,根本沒有半點(diǎn)和她聊天的意思。張躊躇了一會(huì)兒,整個(gè)身子前傾,湊近她:“你說讓他看鏡子是什么意思?”
“讓他看鏡子。”老板娘依舊低著頭,也不回答,重重地
共3頁: 上一頁123下一頁版權(quán)聲明--以上內(nèi)容與本站無關(guān),自行辨別真假,損失自負(fù)
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(diǎn),不代表本站立場(chǎng)與本站無關(guān)。如有侵權(quán)請(qǐng)及時(shí)聯(lián)系本站郵件 enofun@foxmail.com ,如未聯(lián)系本網(wǎng)所有損失自負(fù)!
本文系作者授權(quán)本網(wǎng)發(fā)表,未經(jīng)許可,不得轉(zhuǎn)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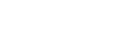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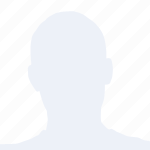
評(píng)論